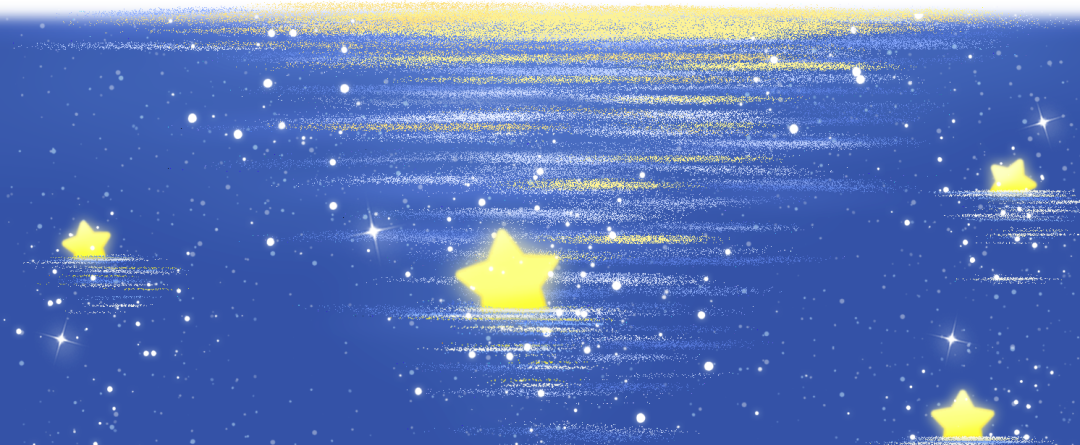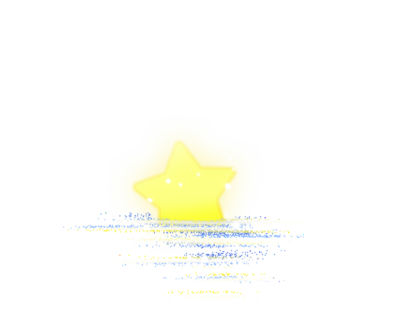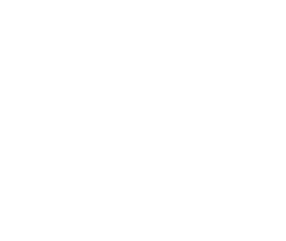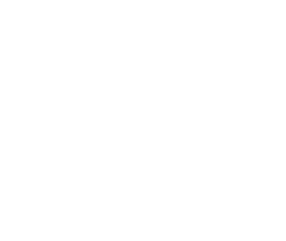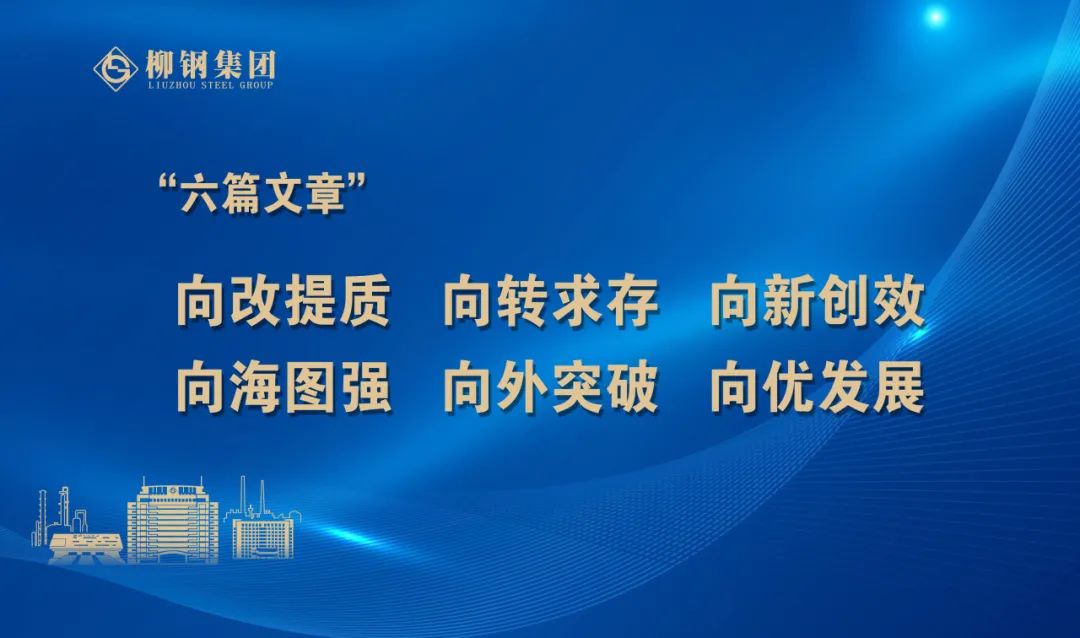{ 海上生明月 天涯共此时 }
有一首歌唱过
“是谁来自山川湖海
却囿于昼夜、厨房与爱。”
想来每个人年少时
都曾觉得这世间天地广阔
历经风霜雨雪,定能大有作为
只是当年岁渐长
动荡不安的心渐渐闯进了更多过往回忆
俯仰之间便拾起了故乡的月光
愿世间的团圆
都不必跋山涉水
□文祧德
向上滑动阅览
小时候,中秋是一块甜甜的月饼,咬一口甜在心头;长大后,中秋是浓浓的乡愁,每到月圆之时便会勾起那份思乡之情。
回想起有一年中秋节,很多人都没能回家。那个晚上,我与同事们一同坚守岗位,一起吃着家里寄来的月饼,聊着儿时的中秋趣事。大伙有说有笑的,有吸田螺时被汁水呛鼻子的,有的月饼突然被调包成五仁叉烧的,还有的赏月睡着喂了一晚上蚊子的……别提多有趣了。
望着那当空明月,我陷入沉思,什么是团圆?是那一轮皎洁无瑕的玉盘、一块酥而不腻的月饼?是一大桌妈妈做的好菜、一家人的举杯共饮?还是一次期待已久的归来,和那被月色浸染了的闲话家常?北宋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:“中秋夜,贵家结饰台榭,民间争占酒楼玩月。闾里儿童,连宵嬉戏。夜市骈阗,至于通宵。”中秋节藏着每一个人内心最真挚的盼望,借着月圆盼着家人团圆,盼着生活圆满。月亮圆了,世间的悲欢离合大抵也都迎来了一个美满的结局吧?
去年中秋回家的人特别多,动车票着实是买不着了。车站里人潮拥挤,我手里一提的红色礼盒格外显眼。盒子沉甸甸的,装着的是游子对归家的期盼。无论走得多远,心中的明月都会一直向着家的方向,万家灯火指引着我们的归途。但愿世间所有的团圆,都不必跋山涉水才能相见。此刻,绿皮火车承载着每一个人对家的思念,就算车厢内再闷热嘈杂,也让我感觉格外心安。
月圆中秋夜,酒足饭饱,我们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聊天赏月,吃着“七星伴月”,听奶奶讲嫦娥奔月的故事。小侄子还在因为分到一个不爱吃的五仁叉烧而生闷气,让我和他玩有月字的成语接龙,经过“激烈”的对抗,最终被他赢走了我的板栗莲蓉月饼。“砰砰、砰砰……”突然一阵烟花掩盖了我们的笑声,那在夜空中灿烂绽放的花朵与月争辉,照亮了整个人间,短暂却又永恒地给中秋节增添了几分喜庆。同沐一轮月,共享一佳节,简单且温馨,这便是我们所向往的美好吧。
草根无数候虫鸣,月在梧桐树上鸣。夜渐深,耳边传来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的旋律:“明月几时有?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,今夕是何年。”古琴的音律使人内心宁静。大地的一切都披上了薄纱,和这低沉悠扬的琴声搭配出一幅生动和谐的画卷。万物仿佛都被赋予了生命,银纱化作嫦娥,在这皎洁的月光中起舞,向着广寒宫乘风而去。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……不知不觉我也沉浸在琴声中,沉沉睡去。
陆鹏 绘
望月怀远
□林鑫
向上滑动阅览
又是一年圆月高悬,桂子飘香的时节。中秋的夜常是透亮的,月光洋洋洒洒地铺满天际,轻拢大地,似在人间点了盏温情的灯。我透过窗户向外望,只见月色投下了粼粼波光,月影星星点点,漏到厂房的缝隙中,洒向望月之人的周身,溜进千万户人家里去。我望着这圆亮的白玉盘,恍惚间似乎望见了许多熟悉的景象。
“小时不识月,呼作白玉盘。”儿时对于月亮稚幼的认知,大抵局限在猜想和许多神秘美丽的神话传说中。我一直觉得那清冷又遥远的月宫之上,当真住着仙子,她舞弄着长袖,轻盈婉转,甚是自在。每个中秋,长辈都絮絮叨叨地和我们说着那些流传许久的神话故事。中秋对于儿时的我来说,也是一个休闲自在的日子。亲戚朋友早早便来了,提着各式各样馋人的吃食,我们几个小孩子一见便跑来,拿了好吃的便又欢快地散开去,每个人脸上都是甜滋滋地笑,比那新装的蜜还甜。月亮悄悄爬上柳梢头,我们便搬出桌子椅子,在宽敞的院子里,就着月色,吃着香甜软糯的月饼,闻着初秋的桂香。明月亮堂堂地照着每个人的脸,大人有说有笑,小孩儿在一旁嬉笑打闹,不知是月色迷人眼,还是晚夜秋风醉人,每个人脸上都热腾腾的,比那新烹的茶水还热乎。
小时候不知离愁别绪是何滋味,长大客居他乡后,月满便添了乡愁。有一句歌词我记得很牢:“那年离开了家乡,从此家乡变他乡。”古人对月弦歌,大抵是因为这温柔似水的月色像极了触摸不到的温柔乡,只是一眼,悄悄藏着的心事便露了出来。自古相思与明月,同三杯两盏淡酒,能酿出佳句诗篇来,却消不掉万般离愁,解不掉各种滋味。
我对着这中秋夜,也生发出心底的思念来。年少时我总是想走出温柔境地,闯荡于世间,领略山川各异,却在真正踏出故园后,囿于漫漫长夜,不知今夕何夕。只是,我也于某个月圆之夜恍然抬起头,那月色轻抚着我,似在温柔地扶起我,无端地使我消散了稚气和固执,收敛了锋芒和气力,让我暂时放下了劳碌和压力。周身一派轻松后,我便想起家中可口的饭菜羹汤和缕缕花香,想起了许多个中秋夜里的欢声笑语,想起了月宫中起舞弄清影的仙子,想起了如今的我再次独自立于中秋长夜……我不禁想,那神仙住的宫殿里,是否也有位仙子立于桂树旁,默默感伤,遥寄相思。月华正浓,我望着它,它也望向我,这般熟悉,这般温热。
我怀念的,是儿时的无话不说,欢声笑语,家人团聚,友邻相亲;我怀念的,是此时远隔千里之外洒满月色的家乡故园,和久留不散的桂子清香;我怀念的,是离我远去的童年和抓不住的流年……又是一年中秋佳节,我望着这轮圆月,看着它慢慢往家的方向倾斜。
汤文斌 绘
外婆的“土”月饼
□黄苏珊
向上滑动阅览
在我四岁的时候,爸妈在外工作,因为无暇顾及我和姐姐,便将我俩寄养在外婆家。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,物资相对匮乏,中秋节来临,外婆也只能买到几个月饼。家里人多,为了让大家伙儿都能在中秋夜吃月饼赏月亮,外婆就做了“土”月饼。
所谓“土”月饼,就是油炸坚果饼子。那种味道,至今令我痴迷,难以忘怀。
中秋那天,外婆早早便起来,到集市换了几斤糯米粉,还买了红糖。回到家,她搬着小板凳坐在院子里开始剥花生,为了使面团口感好,外婆特地将泡好的黄豆装进纱布袋,用棒槌碾磨出豆浆,与红糖和糯米粉混在一起和面团。九点钟的太阳暖洋洋的,照在她的背上,闪闪发光。我和姐姐、表弟从床上爬起来,凑到外婆跟前,闹着要帮忙。外婆说:“你们哪里会做,搬张小凳子,坐在旁边看就好了。”“会!我会做。”“我也会!”我们几个围着外婆,搂着她的肩膀,嚷嚷着要参与进来。外婆被逗得咯咯笑,只能投降,让我们去洗手,帮忙一起做。于是我们婆孙几个坐在院子里,做起了“土”月饼。外婆将和好的糯米粉面团分成一个一个的小团子,给我们一人一个,首先是放在手里,将团子捏成圆饼,然后做成自己想要的样子。我们有的捏成了五角星,有的做成了弯弯的月亮,有的也做成了圆月,形态各异。在我们几个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,外婆已经生起了火,将猪油倒进锅内,热起了油锅。最后一步就是将做好的饼放在竹漏勺内下锅油炸,然后在饼上撒上几颗花生。我们围坐在一旁默默地观看,外婆手持竹漏勺,在热热的油锅里慢慢地来回旋转着,饼子受热渐渐脱离了漏勺,泛出金黄的颜色,香气扑鼻而来,馋得我们几个小鬼不停地问:“好了没有,可以吃了吗?”外婆和蔼地笑着:“待会凉一点,再给你们吃。”花了半天工夫,二十几个“土”月饼就做好了。
晚饭过后,外婆外公带着我们几个,和小姨、舅舅坐在院子里赏月。我们几个捧着香甜脆口的“土”月饼,在院子里嬉戏打闹。外婆看着我们,又开心地笑了。
梁奕馨 绘
来源:柳钢报
朗读:吴婉毓 杨章玉 苏子君
编校:熊汉青 辜姝